1901年(上下)

作者简介:
王树增,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作家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1968年赴临汾市乡村插队务农,1970年应征入伍,历任空降兵某部战士、班长,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鲁迅文学院教师,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编剧。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一级编剧,著名作家。作品曾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内容简介:
世界读书日特刊·专家荐书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的推荐理由:这本书2001年昆仑出版社出过,去年海南出版社又出了一版。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海南版要好些,如果从阅读的便利性方面来说,昆仑版更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丑之辱,历史的复杂幽深之处,被作者笔力千钧地铺陈出来,给了我们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莫言 王树增:回到《1901年》 -------------------------------------------------------------------------------- ★《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 莫言:树增,首先祝贺你在《远东朝鲜战争》之后又写出了《1901年》这样一部大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具有以往纪实类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宝贵素质:客观性。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我很想知道,面对浩如烟海的素材,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判别和选取的? 王树增: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述都难免评价,因此,“客观”地叙述历史只是相对的。这个客观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进程的客观,还包括“评价”上的“客观”———这个客观也许更有意义些,因为对历史的回顾,其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某种困惑。 写《1901年》的时候,我对野史笔记给予了极端的重视。我赞同鲁迅先生的论断,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上讲,野史笔记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一个取舍问题。我对史料的判定原则是:有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者,剥其伪装反向取证;对人物、时间、地点有明显编造者,究其为什么编造后弃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者,当戏剧剧本看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者最有价值,其忸怩之处往往就是真实所在。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们一起专程去保定参观了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我正在创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门的布局和结构,以免犯了技术性的错误。你的《1901年》中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座衙门里当过总督,而总督府对面的莲池书院里也发生过触目惊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参观中,你想了些什么?你还记得总督衙门前那座刚刚修建起来的、肯定比过去的要辉煌的牌坊吗? 王树增:当时我感觉你不是去游览一个古迹,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见一个值得纪念的先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对历史中的“权势”存在一种畏惧和仰慕,仅仅看见总督府里的那顶官轿就足以令我们这些草民心灵颤栗想入非非了。当时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结果被看轿子的工作人员教训了一顿,似乎你的闪光灯一闪,轿子就可能灰飞烟灭。其实,整个总督府、整个清王朝就是一顶大轿子,尽管你我的先人当年无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进莲池书院就看见了民国要员修建的别墅,然后就是几对耳鬓厮磨的恋人,只有你我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一路东张西望。1900年夏天,70多岁的清廷重臣、户部尚书、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绮自己搓好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书院的偏房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他到底死在哪间屋子里,于是我觉得每间屋子里都阴魂缭绕。 历史是平民创造的,历史是平民的历史。我对当今电视电影中那个拖着辫子神气活现的“皇上”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说到历史的辉煌的话,和那些个“皇上”无关,包括风雅的乾隆和懦弱的光绪。《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在《1901年》中,我过多地使用了“平民”这个字眼,这是中国人不太习惯的名词,但我觉得只有这个名词才具备广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亲”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过得远不如今人想象得那般滋润豪华的官吏们。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国从来没有辉煌过,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辉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个小广场,孩子们在嬉戏,恋人们在亲昵,倒是一派温情。这是我们留恋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 ★我对“纪实文学”这个名称感到疑惑 莫言:在你的这部著作中,涉及到了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等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我想知道您如何评判这些人物? 王树增:许多人都自称懂点辩证法,但是到了用的时候又大都糊涂。 《1901年》第一章中关于康有为的篇幅不少,我喜欢这个性格和行为都颇奇特的知识分子。他是试图改变中国政体的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但也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士”,这就使他在100年前居然主张在紫禁城里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同时又对封建帝制的留恋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这水火不相容的两面,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对李鸿章的评判更是历史上的一大难点。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们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阴险的卖国贼,好像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没干别的事,整天就忙着把中国人往深渊里推了。可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在享受着百年前洋务运动的成果,而李鸿章恰恰是引导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洋务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首脑。恐怕最不好评价的就是袁世凯这个人物了,因为他不但是封建帝制下的二品大员,到了民国他居然当了一届共和制政体的总统。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比他更复杂的人物了。 我不是历史学家。在任何场合我都心虚地宣布:《1901年》不承担对历史上那些不一般的历史人物定性的任务,当然也就无法承担歌颂谁或谴责准的任务。 莫言: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认为《1901年》是一部既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但同时却又妙趣横生的书。我想,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你在书中使用了许多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的素材。譬如辜鸿铭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参加对外谈判,怒斥他当年的学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譬如李鸿章去日本谈判被刺;譬如李鸿章访俄竟然由一个俄国商人接待,等等。《1901年》里许多生动得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你认为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王树增:“比小说还要小说”的细节不是小说,是历史事件。写小说的人对所谓情节的编织其实远不如历史生活本身奇妙生动。 和《远东朝鲜战争》一样,在《1901年》中我没有做任何历史事件上的虚构,不是我不会,是不能,也不敢。《1901年》的写作艰难得多,仅仅依据正史不甘心,大量参考芜杂的野史笔记也头疼。近代野史和笔记虽然率真天然,但多如翰海,良莠混杂,年代久远,考证起来颇有难度。我的原则是,我认为可信,或者我拿不准但有提供给读者判断价值的史料,小心慎重地采用。 莫言: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所谓的纪实文学,已经有走到了穷途末路之相,有的人甚至将此做为求名求利的手段。前几年历史散文很红,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但这些文章篇幅都比较短小,像你这样,用洋洋60万言的巨大篇幅来全方位地描述一个封建王朝的断年史的,实属罕见。接下来,你是否还要按照这条路子写下去? 王树增:我不知道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纪实文学”这个名称是不是中国所独有,我一直对这个名称的定位是否恰当感到疑惑。“纪实”和“文学”似乎有点不搭界。文字的东西大概只有虚构和非虚构之分,国外把除了虚构的文字之外的东西统统称做“非文学类”。看来“文学”二字不是可以随便标榜的。《1901年》只是一种文体样式,叫做“纪实文学”有点不敢当。 除了写字,我不会于别的。以后还要继续写点“非文学”的东西,直到写的东西没人看了为止。 (《1901年》王树增著,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43.00元) 《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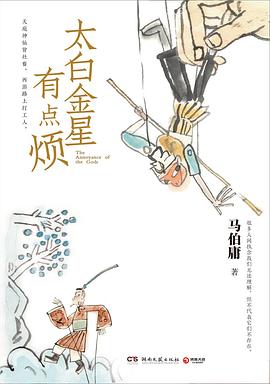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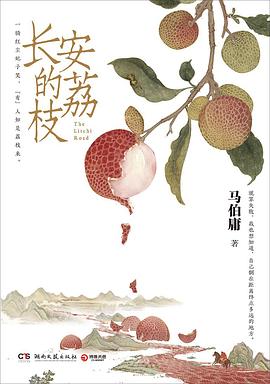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