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内容简介:
鲍耀明 知堂老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雨天的书》) 时光过得真快,《周作人晚年书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将七年,为什么要自编自费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已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纪念我与知堂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参考而已。出版后在社会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纹,不少朋友来信或发表文字给我批评与鼓励,试举其中一二:“这是一本好书”(刘以鬯);“您确实做了一件大善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献史料”(裘士雄);“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的珍贵史料,也是一段难得的情缘,都是不可不读的”(王得后);“鲍先生从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断通信,总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这部《晚年书信》当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桥);“周、鲍二人素无谋面,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鲍耀明虽然始终 没有见过周作人一面,却有着这样频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没有这样的第二个朋友了”(罗孚);“观人论世,如能以小见大,即于琐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为人……这是一个极新颖的整理,出版方法,编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极为仔细,从而令读之者在脉络分明的时与事推移之中,看到一个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物资’与‘精神’两方面,有哪些‘试探’与‘考验”’(戴天);“最近欣承邮友鲍耀明先生以他编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巨册见赠,连日挑灯夜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还是爱不释手,要再读、三读,细赏细析,深觉余味无穷,认为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奇书,值得推荐给有意于研究近代文艺和历史的读者”(潘安生);“知堂晚年书信,是极珍贵的材料,先生决心自费出书,实是一大功德”(舒芜);“《书信》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昨晚我已通读了一遍,这是我多年想读的一本书,获益匪浅”(李勇);“顷接尊编《周作人晚年书信》,甚感欣慰,先生诚有心人也”(刘绍唐);“《晚年书信》收到了,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得之甚为 高兴,感谢不尽”(钟叔河);“谈周作人,要提一本书,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这部书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可作研究”(岑逸飞)。…… 朋友们誉多于贬,令我感到惭愧,有些批评则属于政治性的,我就不再录了。不过,姑勿论内容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是出自于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虽已“盖棺”却难予“定论”,但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周作人晚年书信》这次重版改题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能在内陆重版印行,完全得力于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亲自将原版对照手稿逐一仔细校订,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错讹,使拙编在文本上更加严谨准确,在此谨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二00四年三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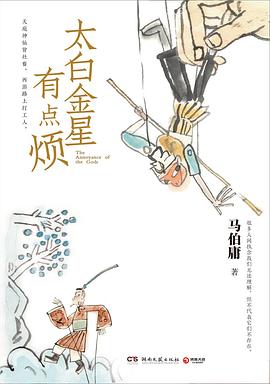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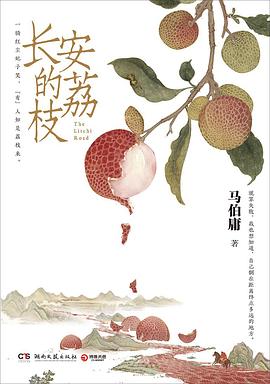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