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经典作品选

作者简介:
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为玉堂,1912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修语言学,1919年秋赴美国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923年夏获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正式提倡“幽默文学”。1934年办《人间世》,次年办《宇宙风》,并提倡半文半白的“语录体”。1935年用英文撰写的文化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并畅销,1936年携全家赴美。本着“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宗旨,出版了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并编译出版了中国的古典著作如《孔子的智慧》、《庄子》等。同时还进行了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尤以《京华烟云》最为著名。196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负责主编《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葬于台北阳明山。
内容简介:
林语堂,幽默的智者 作者:清秋思幽 曾与鲁迅并肩作战,曾留给我们对生命与艺术的深邃思考,林语堂先生是这么个幽默的智者。他的语言平和,哲性,娓娓道来中蕴涵了多少智慧。 鲁迅与林语堂,好比天平的两端。一个激愤,尖利,呐喊声如雷灌耳;另一个则是静逸,沉着,令人思绪飞扬。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甚有差异,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反对新文坛人物的艰涩偏激性攻击,于是与鲁迅先生的唤醒酣睡之人的心态甚是相左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处于那种水深火热之境地,确实极其需要鲁迅先生这般的呐喊!有人提到,语堂先生离开中国是因为鲁迅对其的文字攻战,其实不然。鲁迅逝世后,语堂先生曾非常沉痛地写下那篇“鲁迅之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语堂先生的确是一厚实恬淡的哲人。对于他的为人处事和生活哲学,我们可从其所提倡的“幽默”与所著之“生活的艺术”中深入了解到。 林语堂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那个时期他主张谩骂主义,后来一改而提倡幽默文体。他这么解释“幽默”:“新文学作品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正如他所言,“谑而不虐” 盖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尖酸刻薄,已非幽默。 幽默家视世察物,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他的“论语半月刊”就是以提倡幽默为目标的。 在语堂先生的语录中,他谈极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引自“一夕话”)的确,我们国人缺少幽默,至今仍是如此。现代的名作家中好象也找不出类似于语堂先生的人。李敖,余杰,他们的风格太出挑,狂桀。比较稳重内敛的王小波在于幽默显现上也不足。(这些也是基于人之个性与风格的相异,不便作什好坏高低的定论)其实要达到语堂先生所言的“幽默”,是何等之难事。非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博大胸襟与坦荡,而且这民族也要有一种能让此“幽默”生长发育延伸的氛围与养料。 可我们的社会呢?众人喜欢枉自攻击相异之群,以博片刻痛快,非言者了了几句就把人事给否定了,于己之立场定他人是非对错,且又不能从人性角度来番考虑,所引之理无非是准则理论云云。“幽默”,它的精髓容于宽容与诚恳,若无此品质,即便是广览博阅者也无从谈起,欲仿幽默,其所道之言亦属尖酸刻薄,伪幽默也。 他有一篇文章写到女人,他说: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于”想做另一人“中他说道: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就那”老大“两字,先生作了如此精辟巧妙的分析,谈古论今,引据列证,好一个透彻!(未曾读过的朋友不妨读一读,实在是受益非浅。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诙谐深邃的言语带给我们多少想象与思考的空间。读着便就有那会心的一笑。他的幽默确实是蕴涵了深刻的智慧。语堂先生说过,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那么语堂先生就是在痛苦中把精神升华了的智慧者。他以深邃的哲思用平和言语向我们道来,对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纯朴的生活之艺术。哦,可是,可是时代有它的缺点,人类有他的局限。 是有很多人尊重理解你,但受影响者未必能将这种态度作为处事原则。社会的茫然,文化的没落,精神的颓废,这不由得又令我想起语堂先生的另一句话,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确实是这样,我想语堂先生却是一位可以为自己骄傲的人,我们同样为他自豪;他是乐以满足的人,“生活的艺术”中我们读到了真实,一个恬淡的智慧者。 我也崇尚他提及的“生活之艺术”,在那些精短简练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发觉智慧的火花,不惊意中就得到了喜悦与宁和,如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品着杯醇香悠远的龙井,是如此谢意与舒畅。正如他在“悠闲的情绪” 中说道: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于生活之艺术中,表达了对老人的赞美,对真理与艺术的剖析,对自然之美的歌颂,透过那些哲性的文字,我感悟到那颗纯洁高尚的灵魂。 语堂先生是知道满足,懂得如何去挖掘生活中的真理与美之人。在他那篇“大自然的享受”里,我们又读到了智慧与真实。“人不应该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他对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开的花儿,感不到满足,他还是自杀的好,不要再徒劳无功的企图追求一个无实现可能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也许可以使上帝感到满足,却不能使人类感到满足……所以不要埋怨人生的单调。 先生为中国文学作了很多贡献。他于1924年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又创办过“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在美国时又写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的一生颇为辗转,度过八十一个春秋,于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逝世。 语堂先生,你现在是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了。当你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心灵一定非常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么就好好休息吧,我尊敬的智慧者。 林语堂的文化双语意识 张沛 “语录体”是一种古代白话文体或写作方式,属于汉化的外来文体,初期多为禅师传道记录,后宋明理学家亦纷纷效仿。禅宗是呵佛骂祖的汉化佛教,理学(尤其是“心学”)则是儒门的禅化“异端”,他们用当时的白话发表一己的“个性命题”,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大说”(grandnarrative)造成了某种冲击。林语堂之“语录体” 未始没有这样的特点。林氏本为白话文学健将,但在1926年受军阀通缉南逃、厦大办学受挫、特别是次年春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导致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他对时局世事深感失望,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氏把目光投向了晚明,在此他找到了精神的诗意栖居地——“性灵”、“幽默”,及其语言载体——“语录体”。在此之前,林氏曾实验过西式的语录体,如《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其中显然有尼采及《旧约》的影响。此后不久,“新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林语堂采取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既反对左翼作家的革命热情,亦不满梁实秋等人的欧美古典主义理想,于是提倡一种闲适的艺术情趣来对抗所谓的“新旧道学”。在周作人的启发下,他开始醉心于明清性灵小品,写起了“语录体”文章。 此时“文学革命”硝烟甫散,“革命文学”风头日健,稍后“大众语文论战”与“民族形式讨论”又接踵而至,其中一元独白的苗头已隐约萌现,而林语堂株守一隅古调独弹,其中虽寄新声,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未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林氏本人则在自卫还击中,将“白话四六”、“新道学”、“革命”一概标上了否定的“记标”。甚至在晚年定居台湾后,林氏又说当年鼓吹“语录体”是“在对症下药,针对当时人的口罗哩口罗嗦毛病”。这个说法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录体”的出现只是一个有关文体的文学语言学现象,林氏之所以对“语录体”产生兴趣也不过是他对汉语写作的一种尝试罢了。其实不然。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社会是语言的社会,语言是社会的语言,语言中沉淀了大量的个人与集体记忆,隐含着无数的价值判断,同时更蕴藏有不同的情感音调。语言的这些“隐性基因”中蕴含着极大的行为潜能,在社会动荡、文化转型时期就会从蛰伏状态中激活,以“杂话”或“多语”的面目成为社会/文化革命的主导与先锋。五四时期及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处于这样一场文化转型的“语言狂欢”之中,其中每一句话语均成为“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导向的音调和语气冲突交错的微型战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可作如是观,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也未尝不是如此。 在这场革命化、政治化的“狂欢节”中,林语堂用“语录体”充当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方言”或斗争策略。 宋明“语录体”是以一种外来的非正统文体表达一种新兴的“异端”思想。起初它固然是一种“小说”(micro-narrative)或“个性命题”,但当它经过“社会化”成为集体意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用巴赫金的话讲,即“加冕”——之后,语录也就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口角亲切的白话下面恰恰裹藏着向心、单极化的“道学”内容。也许林语堂正看中了这一点。当然,他所倡导的“语录体”决不仅仅是对禅师、理学家语录的克隆再版,而是他有意识地参照西方文化来反观本国传统,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择学”。 首先,正如巴赫金所云,“人们只有通过参照几乎等于母语、但又非其母语的他人语言,才有可能客体化(objectivize)自身使用的特殊语言及其内在形式、世界观与特质”,而林语堂恰好具有这种“双语意识”。 其次,林氏的“统觉背景”亦异于常人。“统觉背景”包括“所知”与“所设”,二者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格局。如鲁迅出身书香之家,旧学渍润极深,但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故能痛感其中“所设”之荒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林语堂不同。可以说,林氏在赴北京清华大学教书之前,一直是名不自觉的文化失忆—失语症的双料患者。后来他曾多次愤怒地回忆说,他很早就知道《旧约》中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但直到三十岁时才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为此他感到“惭愧”和“羞耻”。这是所谓“文化震惊”(culturalshock)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林氏那里一度冻结的传统文化记忆就此大大激活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获得的不无缺限的“所知”,与“所设”的“光荣化”(glorification)构成的失衡格局,再加上他的“文化双语意识”,“语录体”便因其糅合同/异、中心/边缘、权威/异端的特质而进入了他的视域。 林氏语录体反映了他的文化双语意识。确实,“局外的观察”往往可以对客观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并重新发现自身;换句话说,通过切换视角,认识主体往往可以发现自身的“视域剩余”,即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身,并发现在自我打量自我时所难以认识到的自我特征,从而得以全面、整体地保握自己、完成自己并超越自己而达到主体的“超在”境界。但这只是就其理想状态而言。事实上,当认识主体以他者目光反观自身时,其主体的自足性往往面临解体的危险,或至少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即有可能因此异化为认识客体或被注视的“他者”。林语堂作为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机制之外的边缘人,他不可能也未曾具有鲁迅那样的文化主体意识,对他产生“特殊摄力” 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充任了被注视、被打量的“他者”;而由于林氏对传统文化“所知”相对不足,“所设”部分遂篡取了较大的“完形趋向”,被注视者乃以一种完好统一的图景展现在注视者的面前。这种文化观照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认识:“局外的观察” 确乎使林氏窥见传统文化的某些“视域剩余”与“外在性”,但认识者却也为此付出了牺牲主体性、历史感与使命感的高昂代价。 1926年的白色恐怖结束了“五四”运动的青春期,五四人开始沉静下来,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审定传统。鲁迅等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批判态度,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的语言表现就是对文言、古文的彻底否定;白话与革命、创新、进步等正面价值观获得了等价的关系,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的主导话语,这一本为反对“文言—旧文化”的“个性命题”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排斥“他性”的“大说”和“集体意识”,乃至在破坏旧偶像的同时自身又成为新的偶像,在“加冕”为这场“革命狂欢节”的一元独白之后逐渐异化为他所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自由精神的对立面,其中奥妙颇足思量。 在这个意义上讲,林语堂提倡“语录体”也许是对这种一元独白倾向的警惕与反拨。林氏的“语录体”类似巴赫金所说的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言”,在逐渐成形的一元独白的社会语境下构成了一种否定和批判的力量。当然,一切文化批判均不免受到“市场法则” 的无形操纵而可能沦为批判对象的同谋,批判主体亦或因与众不同而成为社会文化市场上的珍玩(阿多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批判者的初衷。林氏之提倡“性灵”、“幽默”及其配套语言措施———“语录体”,其实也正体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怀疑主义精神。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是错误的。鲁迅深知孱头的“中庸之道”无法推动历史在“正反合”的阵痛中胜利前进,因此“矫枉必须过正”;这正是鲁迅的悲壮选择。这一点,像游离于中国文化主体机制之外的林语堂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真正伟大的人格、思想与作品,应该在引发各代共鸣的同时,首先成为它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不是不需要多元对话,恰恰相反,多元对话是社会文化保持活力与革命性的前提与动力,但缺乏主旋律的对话也会“走调”,徒闻喧嚣,但实际上却成为聋人间的自说自话。林语堂选择“语录体” 为自己的语言—精神家园,固然有反拨、矫正的初衷,但在一个反拨时机远未到来的时刻祭出这一法宝,宜乎哉受到时人的冷落,而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定格,未能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他的怀疑主义因此也止于自适自足而缺少建设性,——这对于今天我们仍处于文化转型阵痛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讲,未尝没有现实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 最早提“幽默”的人 从风格上讲,林语堂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闲适幽默。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幽默”一词的人。2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幽默”,但应者不多,没有形成气候。30年代《论语》创刊以后,他又重新强调“幽默”,并大力创作幽默闲适小品文,这一次则得到了较多人的呼应。最初他只是把“幽默”当作一种语言风格来看待。后来他则把“幽默”理解成“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川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他还说“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可见,林语堂先生已不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手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特定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林语堂先生正是以这样的一种幽默观来看待中国人的幽默的。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过这么一件事。娄时的中国政府曾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而那些在上海办事的部长们,既不愿撤出租界,也不敢冒犯政府的禁令,于是就把在租界内的办事机关都换成了贸易管理局的牌子。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既在表面上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让部长的官府留在了租界里,真是皆大欢喜。在林语堂看来这种花20美金换一块招牌的作法,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幽默。这样看来,林语堂的所谓“幽默”,不是粗鄙显露的笑话,而是幽默中有睿智,洒脱中显凝重。 林语堂的散文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如“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林语堂散文的语言杂收并蓄,各色兼用,像旧时公文的程式用语,时下流行的政治口号等等,都可以在他散文中看到。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的文学语言观念。他主张文学语言可以将文言、白话、上来语及方言俗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文言”式的特殊语言。
目录:
1 读书的艺术 2 论读书 3 谈涵养 4 谈言论自由 5 说诚与伪 6 读书与风趣 7 言志篇 8 论政治病 9 论幽默 10 恋爱和求婚 11 给玄同先生的信 12 论语丝文体 13 祝土匪 14 打狗释疑 15 冢国絮语解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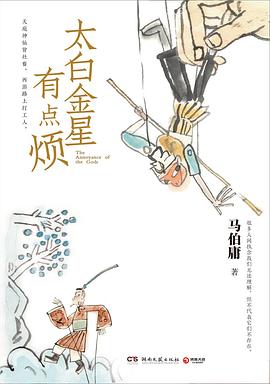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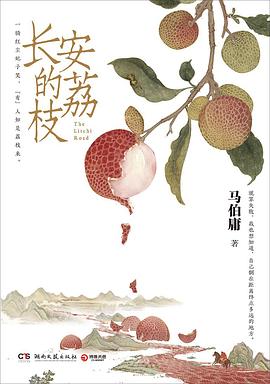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