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破的世界/沧桑文丛

作者简介:
黄侯兴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侨联主席,郭沫若纪念馆馆长,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
内容简介: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本中,肯定会记录“五七干校”这个名词。其源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到了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同年10月,毛泽东又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群众之间派性斗争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大批文化人士在这里洒下血汗也受尽屈辱,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后,有着十余年历史的“五七干校”才告“结业”。 对于这十年间无罪流放的干校生活,除去少量匪夷所思的歌颂文章如“我们迈步前进在广阔的‘五七’大道上”外,大多知识分子留下的是惨痛的、不堪回首的追忆文字,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静远的《我在干校一千天》等。而这部《残破的世界》,更以作者自己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来告诉读者,“五七干校”并不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磨炼革命意志的“大学校”、“大课堂”,而是一所泯灭个性、摧残人格、强制学员驯服的“驯奴场”。而这些“奴”则是来自一支不断被分化被瓦解的群众队伍。“奴”群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权势者的依靠对象,却是造成“天罗地网”、“汪洋大海”这种群众运动的物质基础,其中也不乏告密、诬陷、摇旗呐喊和助纣为虐的丑类。“造奴”之外,便是“造鬼”,无端制造出人群中那百分之五的“大鬼”、“小鬼”、“冤鬼”。并让这些“鬼”长时期面对群众运动的强大政治攻势。“鬼”的对立面,就是“神”了,“造神”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这些近似宗教性的膜拜。对这些荒唐的历史现象,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神运动”、“造鬼运动”是在“造奴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了“奴”,“神”是虚空的;没有了“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而酿成这历史悲剧的“奴”,正是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意志、泯灭自我而屈从于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更为可怕的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 正因为“并不悟自己之为奴”,才会有了那么荒诞绝谬、近似疯狂的一幕幕闹剧:有镰刀不用偏要用手去拔豆秧,而且不准戴手套,大田成了愿意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地主资产阶级决裂的好战场;大冷天进城干活,要发扬“啃干馍精神”,喝碗热面汤也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滂沱大雨中列队观看电影《地道战》,是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好机会;放着电灯不用,每人都要买回一盏煤油灯来读毛著,这叫“一盏灯精神”;猪倌养猪,活学活用,为了“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而去尝猪食,还立下誓言叫牢树一个“忠”字,狠斗一个“私”字,突出一个“尝”字,坚持一个“亲”字;其它如“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当一辈子老黄牛,走一辈子五七路”,“身居茅屋,心向北京;脚踩黄土,胸怀世界”等标语口号,标榜的都是以“驯服”和愚昧为荣。 这些虽然是发生在河南淮阳“五七干校”的一个侧面,但都真实准确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印记,这些荒谬、疯狂但却难以忘却的经历和创痛,不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即使有神来之笔也是无法描述的。作者在叙述往事时,提出了一个这样令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存在着知识分子群体?因为自古到今,中国的文士只是先后依附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一张张“皮”上,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才又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从封建理学的“灭人欲”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一根无形的、绵延几千年的可怕绳索,把中国的文士——知识分子捆绑得紧紧的,沦为只会舞文弄墨而没有灵魂的奴隶。福柯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角色定位是: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这些标准,没有一条能与中国知识分子沾上边的。 这些年来,“知青文学”备受社会关注,而且一本本地出个不停,不过,当我们再沉下气来认真读一读这些干校时期的纪实,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起那些稚嫩、单纯、感情色彩过于浓重的“知青文学”来说,不甚走红的“干校文学”更显得成熟、凝重。“知青文学”赚人同情与眼泪,而“干校文学”则能发人感触与深思。遗憾的是,中国眼下缺少的正是这样一部厚重的有分量的“干校文学”。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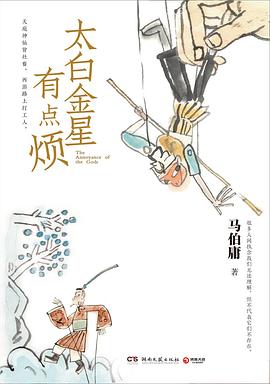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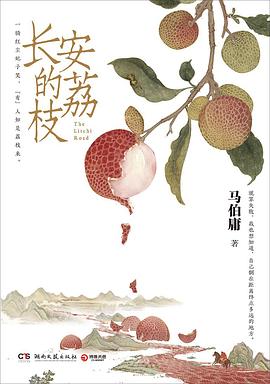
评论